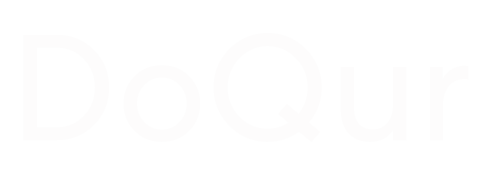翻拍戲的成功範本與類型片的本土實踐
作者:林 萌
有別於通常象徵意義上的犯罪行為驚悚電影,這類題材常常將敘事視角放在“鼠”的一邊,以突出“該遊戲”的解構性、緊迫感,贏得大快人心的話劇效果。此種滑動姿態,影射出社會公義的缺席。《误杀》中的李維傑便是在某一的地域環境下,決心掩蓋真相。影片在嫻熟運用固有敘事模式的基礎上,使故事情節有了紮實的邏輯基礎、精確的感情定位。在該遊戲快感中,對個體宿命進行思索,而並非滿足於講訴驚心動魄的驚悚故事情節。這推進了影片的涵義。
[責任編輯: 劉冰雅 ]
(作者林萌系武漢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
這使電影充滿著了抨擊意味。法本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警員則是法的化身。《误杀》卻通過營造強弱矛盾的氣氛,展現出特權氾濫情況下法制的失效、監管的失靈。平日裡做為“沉默的絕大多數”沉寂於特權之下的底層大眾,或許也只有在同樣繞過法律條文的情況下,就可以展開反戈一擊。
概言之,在文化差異的大背景下,《误杀》能夠消弭異國故事情節與本土受眾之間的錯位,並具備打動人心的力量,除了依靠良好的圖像掌控和演出技巧,還即使在主題層面展現出了情與法之間的對付與抉擇,飽含抨擊現實生活的人文關愛。在翻拍戲的成功範本、類型片的本土實踐這種的多重態勢上,電影開闢了新天地,有著一定的借鑑價值。
無論是羊還是鵝,成功的暗喻常常是商業影片得以昇華的關鍵利器。在《误杀》中,李維傑沒有告訴家人遷移遺體的事實,反倒藉助小兒子在拉韞威逼利誘之下講出的“眼見之實”,令老謀深算的拉韞功虧一簣。一場暴雨見證著拉韞和都彭的失利,也釋放著群眾久經壓抑的憤慨情緒。隨之而來的騷亂將此種憤慨推至顛峰,展現出著“羊群”的力量。
影片中,阿玉和拉韞在警察局裡憤慨相向的特寫攝影機給觀眾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針鋒相對的三個男人,就像兩頭護犢的母豹。此時此刻,理性、身分與話語權都已不再關鍵,她們只做為母親而存有。那個頗具爆發力的攝影機可視作這部電影的縮影。儘管《误杀》在具體故事情節上講了李維傑與拉韞鬥智鬥勇的驚險過程,但實質是一個保護父母的父親的情與拉韞背後的法之間的博弈,而促進拉韞凌駕於法之上的,恰恰也是她對女兒的愛。
做為一部較為成功的商業化類別電影,《误杀》在暗喻設置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羊的詩意,在影片中數次發生。《误杀》的英語名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即“沒有牧人的羊”。“沒有牧人的羊”便是沒有法律條文庇護、引領的群眾。影片裡,桑坤為的是懲處李維傑,兩槍擊斃了路經的羊,這一場景的意味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沒有牧人的羊”也能指沒有方向的一味族群,這也是被李維傑藉助進而得以翻盤的力量。李維傑藉著現代人的憤慨,在墳墓屍檢的故事情節中反敗為勝,就像《让子弹飞》裡張牧之不斷勾起鵝城老百姓對黃四郎的恨。
只好,電影的敘事之核便成了糾纏在情與法之間的人性交戰。就此而言,再沒有比三個父親針鋒相對的特寫場面更震撼人心了。她們都為情而生,相同的是,拉韞有特權(扭曲的法)的護持。拉韞的妻子都彭的巨幅選戰海報就掛在玻璃窗旁邊的門上,始終做為強大而壓抑的大背景發生。這無疑暗喻了自己做為特權階層,便是底層大眾身上遮天蔽日的強大陰翳。
但李維傑對“羊群”之憤慨的藉助,和偷天換日的違規行徑仍未令其滑落倫理與公義的高地。相反,《误杀》將觀眾們放在一種“與李維傑同在”的尊重視角,使其動機顯得可被理解甚至讓人反感。這與影片熟練地化用了貓鼠該遊戲式的敘事模式密不可分。貓鼠該遊戲式的故事情節,在犯罪行為驚悚電影中並不少見,甚至能視作一種成熟的亞類別。“貓/警”與“鼠/匪”的二元矛盾,是這一類別電影的主要亮點。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仍未乏味地說教,告誡觀眾們法的意味或警員的職能,也未貼切而單調地抨擊特權。相反,它通過一場驚心動魄的“貓鼠該遊戲”將自然主義關愛灌注其中,寓言化地鋪陳出來,進一步增強了震撼力。李維傑通過觀看一千部電影贏得了反偵察實戰經驗,運用電影裡的蒙太奇技巧,將一場打著公義擦邊球的“誤殺”變為了他和拉韞的鬥智鬥勇。拉韞則是一名穩重而老練的女警長,破過一千個案件,在刑偵方式上很有一套。一千部電影對戰一千個案件,李維傑與拉韞的對手戲充滿著亮點。
今年年初公映的《误杀》,不久前入選第33屆中國影片金雞獎提名名單。儘管最終未有斬獲,但對一部小效率的改編影片來說,能夠贏得“最佳故事片”提名已屬難於。此前,整部影片已在巴基斯坦本土被改編了不止一次。怎樣在中國語境下推陳出新?這一難度可想而知。
เว็บไซต์นี้เป็นเว็บไซต์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พยนตร์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เกี่ยวกับโปสเตอร์ภาพยนตร์ ตัวอย่าง 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 ข่าวสาร บทวิจารณ์ เร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ภาพยนตร์ล่าสุดและดีที่สุดและ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ออนไลน์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ธุรกิจหรือ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โปรดส่งอีเมลถึงเรา (ลิขสิทธิ์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