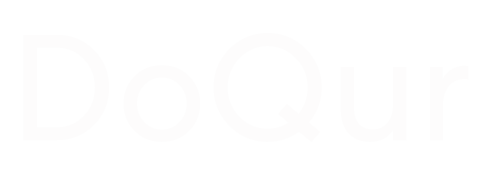20年後,他依然是華語影片最高點
楊德昌輕蔑,連買個自行車都要分期付款,算什么狗屁中產階級。
但這一腔熱血很快就涼了,他斥責「这些王八蛋只教技术,不教创作,一点都不屌,还自我感觉良好」。
殺青那天,楊德昌就跟中影的攝影師鬧翻了,他看不慣這老古董的作法,每拍一個攝影機兩方都要嗶嗶一通,楊德昌險些上去揍他。
電影拍完後十多年,侯孝賢一直都沒敢看,他說「这件事情让我感觉,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
也許正即使如此,現代人總說,跟楊德昌最好的相距,就是做他的觀眾們。
相比之下,楊德昌算是幸運的,父親是中央印製廠的副廠長,母親在信託局下班,工作平衡,總收入豐厚。
在規整的世界裡,刺頭楊德昌註定難以被放置。
影評人焦雄屏公開給三位新人評分,不論從哪個角度看,楊德昌都是水準最低的這個,他從一開始就獲得了幾乎所有人的肯定,成為了電影界的香餑餑,只是燙手又燙嘴。
明驥憋著一肚子火,把所有的電影院副經理找回來溝通交流,說「过去观众抱怨电影偷工减料,这次我们好好回馈观众,让他们一次看个够」。
戰略合作人一致譴責,但侯孝賢堅持要在虧損的情況下,再投五萬。
不用在複雜的舅舅關係網中打滾固然很省心,但這也讓他在與人朝夕相處的過程中直來直去,很讓人棘手。
後來倆人戰略合作《青梅竹马》,楊德昌拿不出錢,也找不到人,侯孝賢就把他們的新房子抵押,還拉上了蔡琴共同參演。
從反戰運動到性解放,從波普表演藝術到搖滾樂,哪個叛逆玩哪個。
楊德昌家中最壯麗的,就是非常大的白板,下面畫滿了各式各樣複雜的人物關係與該事件邏輯,像是一個個精密的蜘蛛網,讓人看了直呼大神。
電影的海報上,是洋洋小小的背影,他就像楊德昌那般,把攝影機對準了社會的後腦勺。
他曾說「你的生活体验就是你的电影存款」,實際上,後來他的影片總是聚焦在中產階級或以下的社會階層,而不像侯孝賢,拍的多半是在貧窮線上掙扎的底層群眾。
賈樟柯曾寫道:「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
這幫人讓楊德昌找出了組織,他積極主動搜尋著關於新潮流的報道,但越看越來氣,那些報道並非被刪改,就是被誤會,每晚上著各式各樣人的騙。
後來洋洋就討厭拍人家後腦勺,他說:「你们自己看不到,我拍给你们看啊!」
1980年,摯友餘為政曉得他在英國很多器材,想拍點東西,問他是不是興趣回去。
打破僵局的,是張艾嘉,她不但拉來了新投資,還應允參演本片的男主角,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把杜可風請到了楊德昌面前,他笑眯了眼,很滿意。
拍完《牯岭街》,原先開朗的張震顯得沉默寡言,但之後他還是選擇去了楊德昌的子公司,他覺得那兒有著單純的創作氣氛。
他寫了一大摞信罵楊德昌,說他是「小飞侠并发症,谁跟你合作谁倒霉」。
楊德昌一生只留下了七又三分之一部影片,每一部的誕生都經歷過無數次茬架,就算你把他電影劇本里的逗號表達成了句點,他都鐵定要跟你玩兒命。
跟他戰略合作過的人都曉得,他就是個劇組暴君。
中後期配音員時,張震正好到了變聲期,總是達不到市場預期的效果,楊德昌氣得在錄音室大門口大喊:「张震!你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 !」
第二次邂逅蔡琴時,她正演唱曲目《最后一夜》,看著看著,楊德昌雙腳捂著臉俯下了身子,老半天才抬頭對侯孝賢說:「好性感呀」。
原田沒工夫理睬他的矯情,整部電影就算再虧個底兒掉,他啊臉都丟光了,在影片的營銷上,原田下足了hp,三十秒的片花中塞滿了各式各樣噱頭,恨不得敲鑼打鼓,沿街叫賣。
做為無根的一代,楊德昌的家庭關係極為直觀,父親這邊只有一個叔叔,母親一個舅舅都沒有,此外,就只有弟弟和姐姐。
一家人開心得很,唯獨他蹦不起來,說是前途一片黑暗。
罵罵咧咧中,片子拍完了,剪接完之後長達兩半小時四十六兩分鐘,嚴重遠遠超過了通常電影院所能忍受的片長,明驥說你再剪剪?
初中時,楊德昌成為了貝聿銘的小迷弟,立志將來要學建築物,可惜沒考上,最終讀了交通學院的控制工程學院。
過去楊德昌總以為拍戲須要非常大的投資,頓時開竅的他忽然發現,這事兒直觀得要命,當下就去買了些零碎的器材,做起了野生動物編劇。
楊德昌正愁沒有用武之地,風風火火就返回了臺灣地區,既當導演又當女演員,兩個人一同拍了部《1905年的冬天》。
上世紀80二十世紀初,臺灣地區影片真的沒什么搞頭,拍來拍去就是些假大空的政治宣傳片,電影票房慘淡,中影這種的官方機構十多年都沒有新人,我們都在積極主動尋求革新。
20世紀末60二十世紀初,臺灣地區白色恐怖瀰漫著,在此種恐懼的氣氛裡,少年兒童常常以組織黑幫的方式來掩蓋自身的渺小絕望,壓抑的環境下,一位小學生殺掉了他們的戀人。
1947年,楊德昌出生於北京,僅僅兩年多之後,南京政府敗陣,夫妻倆只能被迫遷至臺灣地區。
楊德昌在英國生活的十三年裡,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快速崛起,社會高速運轉的同時,伴隨著現代人內心深處的失落與迷茫。
後來,自己還是舉辦了婚宴,蔡琴執意放不下,也許楊德昌也覺得,她是那么的無可挑剔,能跟她在一同,嗎說不上哪裡不太好。
雖不務正業,但他卻憑藉著傑出的戰績順利大學畢業,倒並非說他「中途变节」了,而是擰著股「跟你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的蠻力,把課業攻滅了,他說這種很酷。
自己確認了題材後就開始加足馬力幹活,他天天泡在咖啡廳專訪小女孩,上來直接問人家第二次來例假是什么感覺,途人時不時側目,生怕那位叔要對少女們做啥。
所以這話只能吼給他們人聽,楊德昌觸怒不起,這貨太有天賦了,再難也要搞定他。
當時,吳念真和原田在中影工作,自己計劃請三位編劇各拍一個片段,共同組成一部《光阴的故事》,楊德昌也在獲邀之列。
讀學院那會兒,正逢20世紀末60二十世紀,西方的青年人開始狂躁起來。
倒並非整部影片牛得沒用,而是編劇極為有種,赫爾佐格曾說,他們的首部影片是用他做木匠時存的錢拍的。
蔡琴苦澀地應允了,她用他們的資源大力支持他的影片,客串演出配角、唱主題曲、做美工...被須要的感覺,讓她很高興。
跟楊德昌在一同會結塊的人,遠不止蔡琴。
一個人脾氣那么臭,惹了那么多人喜歡之後,還是那么倔強,那么野蠻,決不是直觀的智商低。
2000年,楊德昌憑藉著《一一》贏得了戛納影展最佳男配角,沒多久即被確診為結腸癌。
侯孝賢很是難過,楊德昌卻管不了那么多,他與蔡琴陷於了熱戀。
某天中午醒過來,楊德昌忽然深感蔡琴與他的世界觀是多么相同,他悲哀到連下班的氣力都沒有。
文化界的硬茬有許多,但像楊德昌這么「难搞」的,一時間很難找出第三個。
蔡琴始終尋不著同情心,想痛痛快快問個知道,楊德昌把答案回到了答錄機裡,她戰戰兢兢地按下,聽見的是對方的一聲嘆息:「哎...你叫我怎么说呢...」
原田說你最好識相,誰出錢誰是老大,楊德昌說,孟子不幹。
可惜,楊德昌已經離開了十一年,但那個時代的現代人,仍然沒有讀懂他。
每每聊起那個,摯友吳念真就來氣:「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就這種,本片收穫了一千兩一百萬電影票房,所有人走出去都風風光光,只有楊德昌憤憤地罵娘,他覺得這侄子矇騙觀眾們,就並非人乾的事兒。
二十歲生日這天,楊德昌忽然感覺他們無比蒼老,無法再這種下去了。
後來,原田把他所有的經典作品重新看了一遍,總算知道了他當年的憤慨與不甘。
加之看不慣幼兒園裡的種族主義現像,楊德昌憤然休學,前前後後加起來只待了一個學年。
而大眾愛好的荷里活電影,他見一個躲一個,嫌low。
他沒罵原田是王八蛋,即使能幫他找出錢拍戲的人,大概只剩原田一個。
有一天他剛到劇組就被楊德昌劈頭蓋臉大罵一頓,接著被關進劇組的小黑屋裡,要求面壁思過,等被放出來時,他一臉的委屈與絕望,正好拍出了楊德昌想要的狀態。
而彼時的英國是自由的、開放的、是英雄不問出處的,有如天堂。
為的是這事兒,高層專門開了個緊急會議,副總經理明驥當場炸毛:「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的电影,就这么屌!」
但楊德昌相同,他始終是憤慨的、抨擊的,在並不友好的外部環境中奮勇吶喊,他的電影中總是有許多話癆式的人物,恨不得把他對社會的思索統統說出來。
2007年,楊德昌逝世,石碑上只寫了一句話:愛與希望之夢不滅。
他為我們揭開了生活的謎底,順利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也就離開了我們。
藉著探討工作的由頭,楊德昌總是三更半夜去按她家的門鈴,單純想找人宣洩一下鬱悶的心情,原田說,整部影片把自己拍成電影了彼此間的恐怖份子。
當時《风柜来的人》並不理想,公映六天就被迫撤檔,楊德昌覺得太可惜了,提出要幫他重新配樂。
為的是安置軍官親屬,中央政府創建了眷村,這兒住著的都是「外省人」,他們既難以適應當地的生活,也難以憑藉著自己的力量返回家鄉,此種漂泊感不但存有於父輩頭上,後裔們也同樣。
1990年,楊德昌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式提上了日程,這是他最想拍的一部經典作品,帶有著強烈的回憶錄美感。
整部影片,楊德昌醞釀將近15年,像是他以往經典作品的大總結,失望中帶著溫暖,抨擊中帶著悲憫。
他接演的這段是《指望》,講訴一個初來月事的女孩,對美女春心萌動的故事情節。
電影帶著股濃濃的戾氣,就像李立群出演的配角說的那般:「我也想一枪崩了那狗男女,狗领导,可是什么都做不了。」
日復一日的更替中,現代人對此的體會是較慢而遲鈍的,但對楊德昌而言,那些是簡單且頗具張力的,他所有的經典作品,都在深入探討那個問題。
兩天在上班馬路上,他被奧地利編劇赫爾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電影海報吸引,在電影院度過了天翻地覆的兩半小時。
費了老鼻子勁,侯孝賢憑藉著整部經典作品被提名金馬影后,最後以一票之差輸給張家輝,也算是美景。
結果,兩人合拍了一個禮拜後,吵得不可開交,楊德昌在劇組就要把杜可風「驱逐出境,原地送走」。
中學時即使看同學鬱悶,頻繁轉校,戰績爛得很。
而且電影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張艾嘉與胡因夢的仙人陣容,更關鍵的是,現代人從他的經典作品中開始思考自身所面臨的問題。
「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
後來蔡琴說:「柠檬跟牛奶,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放在一起就会结块。」
但影片公映後三天,即使電影票房太爛而下線,倆人虧得兩眼發黑。
胡適曾說:「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多少正视的勇气。」
楊德昌回了句「少一秒都不行,上不上随你。」
在之後的戰略合作中,他越發覺得蔡琴端莊迷人,還帶著點特立獨行,幾乎是他在返回臺灣地區後邂逅的最傑出的男子。
故事情節改編自一個社會新聞報道:
讓他第一印象最深的就是費里尼的《八部半》,那種看不懂的感覺,讓他覺得高級。
電影公映後,叫好又叫座,明驥說氣死了也值。
還為他們訂製了一件T恤,下面寫了四個人名:赫爾佐格、佈列松、楊德昌。
婚後,楊德昌說:「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
在後來的影片中,楊德昌總是不厭其煩地講訴著被壓抑的少女生活,也總有個孩子跟他兒時一模一樣,訴說著他童年時的種種鬱悶。
高中時更為差勁,碰上了個跟他八字相左的同學,整天想著維修他,他氣得夠慘,誓言一定要跟這神經病死扛。
第二次看見楊德昌,張憤慨呆了,穿著西裝,戴著阿瑪尼眼鏡的他在人群中十分搶眼,帥得沒用,但是噩夢很快就來了。
影片公映後,新鮮的題材快速吸引了數百名觀眾們,電影票房起死回生,新影片運動正式打響。
他讓人咬牙切齒,也讓人無可奈何,都怪他那無恥的天賦。
侯孝賢曾對他說:「如果拍[
彼時的楊德昌還沉溺在上一段婚姻關係的挫敗中,蔡琴的發生讓他的感情生活重新透進了光,但他的愛也就止於此,沒有更多了。
直到心靈的最後時刻,他始終悲觀地懷揣著希望,甚至做了許多實驗性的化療,偏要看一看能不能夠活下去,但這一次,他未能贏。
每晚掛在嘴邊的,除了「给我滚」就是「X你妈」。
家裡人很支持,這幾乎是外省家庭的雙親們共同的理想,他們不希望小孩像自己那般,被情勢牽扯著無家可歸。
但歸根結底,楊德昌是單純的音樂家,他的電影離普通觀眾們太遠,新浪潮過後,市場很快不景氣了下去,而蔡琴的事業紅紅火火,成為了流行曲天后。
自打上了幼兒園,楊德昌就從來沒消停過。
直至生前的最後一部經典作品,他都在斥責曾經的訓導主任並非個東西。
在旁人認為,自己一間過著比中產階層還要高許多的生活,簡直就如女王郡主通常。
強烈地想要曉得真相的他,有了去英國求學的念頭。
1974年,楊德昌領到了加利福尼亞學院的電子工程建設學士學位,渾身輕鬆,終於是對家中有了個像樣的交待,起身他就提出申請去了南加州學院修讀影片專業課程。
在後來的《一一》中,7歲的洋洋問媽媽:「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我们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緊接著拍《海滩的一天》時,楊德昌說中影的攝影師都是渣渣,讓自己都滾,篤定要找杜可風來攝製。
十多年之後,胡因夢在自傳裡說,從影17年,表演的幾十部影片都是「哭笑不得」,稱得上佳作的只有《海滩的一天》。
休學後他去哈佛大學做了一位計算機工程師,一待就是7年。
幾近崩盤的他曾一度想要輟學,雙親不敢,他就整天把他們扔在電影院,專門看那種電影票房不太好,將要被趕入院線的冷門片。
這變相的稱讚,讓楊德昌開心得很,他判定侯孝賢是個好人。
此種無力感也是楊德昌的狀態,他對電影很不滿意,說是被刀架在胳膊上才拍的,雖然它奪下了當年的金曲獎影片獎。
楊德昌給電影配以了維瓦爾第的《四季》和沃爾夫岡的《G弦上的咏叹调》,配樂一換,整個感覺完全不一樣了,影片在夏威夷參展時,現場呼聲陣陣,侯孝賢欽佩得五體投地。
不被規訓,貫穿在他成長的始終,他從輕蔑與他所判定的混蛋和解。
後來,再沒有華語影片像《一一》那般用如此堅硬的形式慢慢地講訴著心靈。
編劇懟了他一句:「他才14岁,你神经病啊 !」
工作自由自在,管理工作很鬆,幼兒園裡還能隨便看影片,氣氛好到降落,但他還是過膩了。
楊德昌給他回電話號碼時,只說了一句:「你的信我看了」,之後傳來的是他氣得發抖的聲音。
電影票房的相繼慘敗,讓楊德昌在找投資時吃了很多閉門羹,原田又找他返回了中影,倆人準備拍一部《恐怖分子》。
影片殺青時,楊德昌找出張國柱,讓他把女兒張震也帶回來試試鏡,張震不樂意,但沒架得住母親的忽悠。
แท็ก 四季 青梅竹馬 G弦上的詠歎調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牯嶺街 一一 八部半 海灘的一天 恐怖分子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 1905年的冬天 光陰的故事 最後一夜 風櫃來的人 指望
เว็บไซต์นี้เป็นเว็บไซต์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พยนตร์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เกี่ยวกับโปสเตอร์ภาพยนตร์ ตัวอย่าง 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 ข่าวสาร บทวิจารณ์ เร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ภาพยนตร์ล่าสุดและดีที่สุดและ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ออนไลน์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ธุรกิจหรือ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โปรดส่งอีเมลถึงเรา (ลิขสิทธิ์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