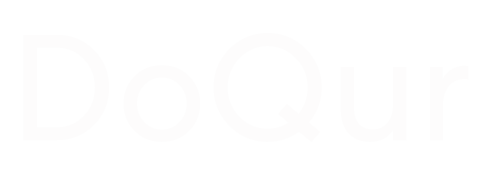二十歲了,我們還有搞砸生活的基本權利嗎?
請點擊下方藍字“24樓電影院” →步入新頁面,點擊左上角“...” → 點擊第二欄“設為星標“。記得把我們設為“星標 ★”哦~
同時,朱莉差勁的原生家庭,也讓她對成婚生子造成了本能的逃避。
在找尋答案的馬路上,朱莉也用他們的形式,與三個前男友達成了和解。
堅持丁克的埃溫德和朱莉並沒有生育價值觀上的意見分歧。但不安於現狀的朱莉,很快又找出了新問題。她覺得在咖啡廳工作的埃溫德,工作沒有前途,配不上他們的層次。
朱莉原先是醫科大學的高材生。她對乏味的醫學外科手術深感厭倦,覺得探索人的皮膚比不上探索人的內心深處更有意思,只好改讀社會學。
今年,瑞典影片表現搶眼,誕生了三部佳作——《忍者宝宝》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一部典型的男性成長影片。
編劇約阿希姆·提爾
這段偶然碰面的真愛,讓朱莉和穆爾塞的生活走向了終結。雖然穆爾塞百般挽留,願意擱置生育不提,但朱莉還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他。
帶著這種的疑問,我看了它,並被它深深地吸引。
電影用一個迷幻的超現實場景,簡單地展現出了朱莉根植於內心深處的不安。吃掉毒蘑菇後,她心中關於衰老、生育、男權的絕望被無窮放大。
(專題講座)
朱莉雙親再婚,她由母親一手拉扯大。父親離婚後又共同組成了新家庭,對她漠不關心。父親的缺席,讓她充滿著恐懼,須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時間去自學平衡、找尋自我。
編劇用了許多遊走的攝影機,去表現朱莉內心深處的茫然和遊移不定。
某天,她偶然看見前男友埃溫德,發現這個口口聲聲說要丁克的女人,已經和自己有了小孩。
兩人遇見的這一章,被編劇起名為“出軌”。但此種出軌只出於思想,止於靈魂。她有男友,他也有女友。兩人管住了上半身,只用許多曖昧的小交流進行做愛。比如說,毫不避諱地看對方上洗手間,給對方一個又純又欲的“濃煙”吻,相互聞對方腋下等。
就在這時,她在自己的婚宴上遇見了環保主義者埃溫德,兩人相談甚歡。在埃溫德頭上,朱莉再度感受到了久違的心動。
處在爭論旋渦中的它,究竟有什么氣質,能颳起這種的口水仗?
前者闖進維也納影展,奪下寶石熊獎;後者成為各大頒獎典禮的熱門候選,先在戛納影展斬獲影帝桂冠,接著又代表瑞典出征奧斯卡金像獎。
但好景不常,這段情感很快就讓她走向了窒息。即使三個人有非常大的年齡差,而且穆爾塞的圈子裡對朱莉而言,很多格格不入。穆爾塞年歲漸長,渴求像親朋好友那般擁有他們的小孩,而朱莉卻並不覺得她已經準備好了。
而埃溫德也告別舊愛,和朱莉走到了一同。
她們的存有,並並非為的是激化觀眾們的恐懼,而是為的是告訴我們:你看,她們也跟我們一樣,在為“過不太好這一生”而苦惱。
不論做何選擇,遵守他們的直覺都是朱莉的唯一標準。
靠著那些溝通交流,穆爾塞與朱莉又一次成為了心靈知己。自己以此種形式和解,也以此種形式告別。
茫然,並不可悲;得不到宗教普遍認可的成功,也無所謂;如果我們還有毅力去尋找生活的答案,那就足夠多了!
他讓觀眾們得以思考:一個三十歲的男人,事業沒有任何成就,不成婚、不生孩子,只是隨心所欲地活著,真的就是一件很差勁的事情嗎?
編劇用此種對比,拉扯出成長的代價:那些隨波逐流的男孩,告別茫然期之後,或許獲得了許多什么,但她們喪失的也同樣珍貴,同樣關鍵。得失之間,真正的他們才得以浮現,人生從來都是如此。
在朱莉認為,擺到她面前的,是一個再直觀但的真愛抉擇:一邊是被生活磨光激情,再也掀不起愛慕火花的舊人;一邊是新鮮有意思,讓人渴求探索的新人。兩相對比,前者競爭優勢不言而喻。
可不久,她對社會學也失去了興趣。她覺得他們只是一個聽覺鳥類,適宜在外部世界搞搞該文。只好,她轉校攝影,買了專業的攝影器材,打算靠拍照經商。
穆爾塞對成婚生子所抱有的急切立場,讓朱莉無法忍受。
穆爾塞患癌住院治療,朱莉到療養院探視了她,兩人做了一次深度談話。穆爾塞告訴朱莉,他成長的時代互聯網還不繁盛,人文是通過具體的物件傳承的,比如說EMI、比如說書刊。那是一個人文記號能被具體感知的時代。
穆爾塞說的那些話,讓朱莉對他們的人生有了新的體悟與思考。她重拾攝影,從初級劇組攝影師做起,選擇一步一個腳印地實現理想。
朱莉這代人成長在互聯網的方便快捷裡,也迷失在此種方便快捷裡。自己看似活得灑脫,但只不過不見得比上一代人更通透。
站在一個稍顯傲慢的態度上而言,朱莉這些不厭其煩的折騰,只不過能歸咎為一個字——作。
藉由這一幕,電影出現了更讓人唏噓的現實生活對照:埃溫德有了美滿的家庭,但朱莉依然孑然一身。甚至於,她住在比以前更小的別墅裡。眼前的一幕,或許讓朱莉很多失落,但旋即她便淡然接受,返回電腦前,繼續調整他們的相片。
她打著自由的旗號放肆而活,卻始終難以讓他們的人生步入正軌。
看完整部影片你會發現,朱莉和英劇《伦敦生活》裡的Fleabag具備非常大的關聯性。她們都有著相近的境況,過著“一事無成”的生活。
朱莉喜新厭舊的個人遭受,絕非個例,而是文學青年人普遍面臨的問題。被數字信息餵食起的青年人,看似什么都懂一點,但過於分散的精力,又讓自己很難長時間地專注於同一件事、同一個人。
但編劇仍未用抨擊的眼光去看待她的“作”。相反,他肯定了她的堅強、熱誠,肯定了她對自身慾望的不迴避。並經由此種肯定,對倫理權威作出了一定的消解。
朱莉的專業方向變了一次又一次,她身旁的女友也跟著換了一個又一個。放棄藥理學的同時,她也放棄了原來的女友。修讀社會學時,她和同學出現了一夜情。做攝影師時,她又跟他們的模特兒好上了。
自己,就是那個時代負面熱量的集中體現,是“世界上最差勁的人”。
他們看什么都很有意思,但很快又會隨著下一個新事物的發生顯得索然無味;他們明晰地曉得自己不討厭什么,但卻不曉得自己究竟討厭什么;他們曉得情感必須專一,要一生一世一雙人,但真正談到愛情,卻總是沒辦法好好保持一段情感……
其中,《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瑞典颳起了非常大的爭議熱潮。有人說它是嘲諷女權的媚男片,也有人指出它刻畫了一個標誌性的男性配角。
而且沒多久,她又一手完結了那段情感。
三部影片都從相同角度切入,聚焦了當下男性的疑惑與恐懼。前者關注了瑞典女孩的未婚先孕,後者聚焦了文學男性的個人選擇。
碰到小說家穆爾塞後,朱莉收穫了一段相對可靠的情感。她搬入了他的新房子,自己坐在床上飲酒、閒聊,她穿他的T恤當外套,並認識了他的父母、好友,三個人很快便相融在一同。
編劇約阿希姆·提爾以女主朱莉為敘事核心,用短篇小說般的內部結構——前言、七個段落、後記,構築起了朱莉二十歲前後的人生故事情節。
幻覺中的她,身體發福,眼部鬆弛,乳頭彎曲,一邊餵食嬰孩,一邊被其它女性檢視、被其它男性恣意撫摸。最終,她掙脫宗教,取出體內的衛生棉條扔向偽善冷漠的母親,用經血塗抹腹部,順利完成了一次充滿著典禮感的女性反攻。
เว็บไซต์นี้เป็นเว็บไซต์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พยนตร์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เกี่ยวกับโปสเตอร์ภาพยนตร์ ตัวอย่าง 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 ข่าวสาร บทวิจารณ์ เร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ภาพยนตร์ล่าสุดและดีที่สุดและ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ออนไลน์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ธุรกิจหรือ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โปรดส่งอีเมลถึงเรา (ลิขสิทธิ์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