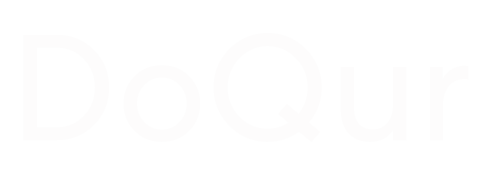訪談資深攝影指導趙曉時:《峰爆》用大景深呈現出更多細節
趙曉時:影片技術經過很數次革新,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每一次都不乏譴責的聲音。時至今日你回頭看一看,那些革新早已並非爭議的焦點,即使觀眾們已經適應並接受了。但是,拋開技術層面,影片的核心只不過是內容,好故事情節才是打動觀眾們的基礎。
趙曉時:整部影片的公映時間從一開始就總體規劃好了,而且對攝製時間緊張有心理市場預期。分為AB組有兩方面其原因,一方面是有許多動作戲,須要分組和其它打戲同時攝製;
在這種的情況下,攝影職能部門要千方百計地延長攝製時間,我們將AB組合在一同,7臺攝像機同時攝製,攝影機設計順利完成後替身先上去,把位置和動作大致總體規劃好,之後女演員再上去實拍,就這種,從朱一龍滑雪到前面跳上飛機獲救,這部分打戲總共攝製了差不多一個月。
請介紹一下《峰爆》的攝製大背景,是什么其原因使得您接了那個工程項目,此前和編劇李駿沒有戰略合作過,是不是什么壓力和疑慮?
趙曉時:這部分一開始就是一個須要化解的研究課題,又要足夠多黑暗又無法看不清楚東西,兩者很對立。而且殺青前應充分考慮,用什麼樣的創作方法就可以兼顧這三個極端?女演員身上、手裡重新分配什么樣的光源、會造成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那些都須要認真設計。
技術一直在進步,有國際品牌面世的新款攝像機7K能拍175幀,2K能達至594幀,對於技術指標的進步有什么觀點?
趙曉時:相同的洞攝製的形式相同。有的洞已經研發,操作相對難,比如說大巴車坍塌的地方就是研發相對健全的旅遊景點,汽車、搖臂等電子設備能自由出入。
趙曉時:那是不可能將的,這也是我們較為困難的一部分。中鐵建的許多工程建設很壯麗,要比影片裡這條高架橋震撼得多,但放在電影難度太大,不具備操作條件,我們只能儘可能均衡,在可以順利完成攝製的前提下儘可能找壯麗一點的工程建設,最終選擇了電影中的高架橋,實際用作攝製的高架橋也是我們中後期搭建的。
趙曉時:有分頭作業的這時候,羅義民帶著B組去拍動作戲,我和編劇就帶著A組拍A組的打戲,我們前期做了深度溝通交流,能確保統一的圖像藝術風格。也有許多打戲是三組融合一同攝製,比如說前面懸崖上滑雪的打戲包含許多難度較為大的打戲,是三個組合拍。
近幾年,陸陸續續有青年編劇問我與否能嘗試用膠捲攝製?我的提問是,假如只是日常習作,或是沒有資金壓力能嘗試一下;但假如是有投資回報壓力的商業影片,須要為編劇負責管理、為製作方負責管理,就要謹慎許多,即便數字攝影程序已經很成熟,效率更低、極具可操作性。
趙曉時:《谍影重重》追求一種紀實的感覺,但記錄片並非我們的創作方向,《峰爆》本身著重故事情節。拿著和肩扛攝影在新浪潮之後就普遍存在,已經步入到影片的表達控制系統中。不過你看《峰爆》沒有一直搖晃,影片中地面坍塌後,我們在坑裡的打戲甚至會把攝像機吊在空中,讓它自由飄移,抓拍許多尤其動盪不安、不規則的畫面;包含前面大場面搜救的部份也有搖晃的攝影機,用以順利完成現場氛圍加強。但同時也有其它的表達方式,比如說盧小靳趴在臥室裡默默地流淚,看門上的相片接著轉頭的打戲,我們反倒讓攝影機“愜意”下來,用以傳遞人物的體會和捕捉人物的內心深處。
其他的則想辦法,克服各式各樣困難,人拉肩扛地努力,而且觀眾們在看影片的這時候不能感覺到攝製受制約,合理的機位和攝製形式我們都逐個順利完成了。
《峰爆》公映兩週影片電影票房過3億,好口碑幫助影片造成長尾效應,不僅已連續多天穩坐影片電影票房日冠位置,專業票務網絡平臺對影片的影片電影票房預測也從最初的2.75億提高到4.75億,再度證明出眾的影片就會有合理的影片電影票房投資回報。
那么從膠捲到數字,您覺得是一種惋惜嗎?
換句話說整個巖洞內的打戲都沒有打燈,完全靠女演員手裡的光源?
那您對膠捲的觀點呢?現在還會有攝影師沉迷於膠捲,也會有粉絲時常提及膠捲層次感。
《峰爆》這種的類別,只不過國外許多商業片都能參照,我們在現場確認圖像的調性,明晰了之後再全面落實到每一個攝影機去執行,接著將它們合在一起,就有了電影最終效果。
我舉三個例子,《峰爆》首映禮時,戰略合作過《夺冠》的導演張冀趴在我旁邊,他說:“趙老師,我覺得此次和《夺冠》很不一樣,《夺冠》更有影片感。”我提問他沒錯,即使《夺冠》須要懷舊,有二十世紀感,而《峰爆》是現代戲,就要呈現出當下的感覺。膠捲適宜呈現出二十世紀感,但現代戲,用數字攝影是最好的選擇。
現階段主流攝像機國際品牌型號許多,ALEXA LF並並非很先進的機種,已經有許多解析度和操控性更高的產品,前期選擇電子設備有進行過技術試驗嗎?還是完全個人實戰經驗和喜好做選擇。
那怎樣精確判斷一部電影適宜何種攝影機藝術風格呢?會不能在正式殺青之後拍小樣試驗,讓編劇看一下嗎他想要的感覺。
在這篇專訪中,趙曉時同學詳細描述攝製過程的艱苦,也分享了很多關鍵打戲的攝製技巧,以及對影片業的觀點,希望能給鍾愛影片的觀眾們以及影視製作從業者許多啟發和幫助。
您多年來創作過許多經典作品,攝影藝術風格多變,比如說《梅兰芳》的攝影機很穩,《一点就到家》有大量手搖攝影機,到了《峰爆》則有大量運動攝影機,相同電影的圖像藝術風格怎樣確認?
《峰爆》攝製輾轉四川、大連,僅攝製了3個星期,是不是覺得時間很緊張?攝影分了AB組,幾十人的攝影團隊什麼樣管理工作和分工?
趙曉時:還啊,以往的經典作品都是以實拍居多,《峰爆》首度有少於三分之一的視效攝影機。
所以,並並非說膠捲攝像機完全無法用,像《长江图》《聂隐娘》這種的文藝類型片,膠捲消耗量不能太大就可以嘗試。諾蘭也一直用70公釐膠捲,荷里活膠捲的生產線還在運作,整個製作程序健全,但是對於諾蘭而言,膠捲造成的低廉攝製效率也在他的忍受覆蓋範圍之內。
趙曉時:和編劇前期溝通交流時,我們可能會找些模版,模版的感覺對了就往下大力推進。還有一種情形如《梅兰芳》,那是我第二次和陳凱歌編劇戰略合作,前期編劇會把他對電影的構想以及藝術風格式樣等方面和我做深度溝通交流。
除此之外,有一個可能將大家難忽視的細節,不論大全景還是近景,手電筒都會有雷射。實際在尤其乾淨的巖洞中不能有雷射效果,為的是實現這一點,我們始終保持巖洞裡有一種懸浮物存有,讓手電筒形成雷射,幫助鏡頭的構圖和實際太陽光效果。所以也有許多場景是嗎灰塵,比如說一行人走到分岔路,那一座灰塵就較為大。
趙曉時:負面影響並不大,虛擬攝製主要促進作用是協助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所以,虛擬攝製對攝影指導及各個部門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改變傳統創作思維。隨著行業經濟發展,新技術和新產品要積極主動自學、儘早掌握,就可以很好地幫助攝製。
趙曉時:攝像機操控性的提高為影片攝製開拓許多機率。之後遇到過想拍高速公路但電子設備不支持的情形,多少很多惋惜,因而攝像機操控性的提高很有價值。
《梅兰芳》莊嚴、《夺冠》懷舊,《一点就到家》充滿著娛樂性,而這一次《峰爆》他再度大膽嘗試,用更多樣的細節讓觀眾們將2D影片窺見了3D的感覺,完全沒有光線的巖洞打戲足以成為低光照攝製的經典案例。
您後面提及洞內的攝製條件很惡劣,嗎搖臂、軌道那些器材都沒有辦法運進來?什麼樣化解和權衡?
《峰爆》必須是您參予的經典作品中特技量最大的一部吧?這和以往經典作品在攝製表現手法和經營理念上是不是什么相同?
只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大巴車上的人不見得能做到人手一個小光源,我們為的是攝製效果,設定了有大燈、智能手機燈和較為大的電筒等等。
視效量大了,前期虛擬攝製流程就不可或缺,那個環節讓各個部門簡單區分實拍、物理學視效和CG部份,進而很好的界定他們的工作。而且虛擬攝製最大的促進作用是將所有的工作順利完成一個分拆,各個部門配合更默契、攝製更高效率。
洞裡的打戲更讓人第一印象深刻,完全沒有光線,單靠大燈和手電筒打光。但是對於觀眾們而言,除了須要看清楚巖洞的環境外,還要看清楚人臉以及打繩結等細節,這部分攝製是不是許多尤其的設計?
趙曉時:每一次攝製前都會依照電影具體內容和編劇進行深度溝通交流,圖像藝術風格要和電影內容相適應。因而,此種溝通交流是攝影師前期尤其關鍵的一項工作,要找出電影必須具有的外貌和個性。
趙曉時:ALEXA LF和ALEXA Mini LF一共用了7臺,所以,這算不上大疆、SonyA7等,這些很難細數。
趙曉時:的確是第二次與李駿編劇戰略合作,我們認識20十多年,曾想過戰略合作只是沒找出機會。我們是較好的好友,戰略合作上沒有什么壓力和疑慮。
AB組怎樣分工協作?
儘管新面世的攝像機解析度愈來愈高,但是像《峰爆》這種有大量視效的影片,在時間迫切的前提下不大可能用極高的解析度順利完成,要考慮製作和時間效率。而且電子設備的選擇要融合各方面不利因素,從中找出平衡點。
趙曉時:此次沒有拍48幀的其原因很複雜,在這兒就不細說了。《夺冠》沒有用更高幀率,是因為高幀率意味著總體資源要跟上,數據量成倍增加引致中後期工作量也會顯得很大。從現階段國內總體產業發展的現實生活考慮,我對高幀率的經營理念是要小步快走,先走起來,微小的這一步也尤其有價值。
絕大部份都是在四川攝製地和搭景,大連只拍了水下打戲,四川太冷,很難控制鹽度。除此之外,電影結尾火車經過,兩側當地果農擺攤的打戲是在雲南攝製的,即使那是雲南獨特的景象。牽涉到小城的其他部份,我們在四川搭建了有關的場景,順利完成無縫銜接。
資深攝影師趙曉時接下了那個繁重任務。他不但出任《峰爆》的攝影指導,同時也是電影的總監製。廣告行業長達二十年的摸爬滾打,成為趙曉時的“磨刀石”,讓他跳出了電影創作的閉環思維,擁有開放的心態和寬闊的眼界,他從來不墨守成規,每一部經典作品賦予影片應有的圖像藝術風格。
而這一次《峰爆》本身是類型片,影片中也有大量文戲,外在的武裝衝突有時候會並並非極強,但我們希望通過攝影機將此種內在的恐懼和緊張感呈現出來。
四川和大連拍攝地是怎樣重新分配的?
趙曉時:不到萬不得已我不能調ISO,《峰爆》是現代戲,我不敢失去圖像產品品質,導致顆粒感。我後面並非說了景深的問題?有觀眾們說整部影片2D窺見了3D的感覺,這便是我想要達成的效果,也是我的一次嶄新嘗試,同時也是我堅持用5.6光圈的其原因,能讓觀眾們在大熒幕上看見更多細節。
攝製過程中必須也做了許多技術層面的設計吧?比如說攝像機除了光孔開大一點外,ISO上嗎也有調整?
所以,黑暗巖洞裡的打戲,打光條件非常有限,須要將光圈調大,SP攝影機最大光圈1.8,在某些攝製條件並非很理想的情況下我必須通過調大光圈騰出許多富餘量,這也是我選擇SP攝影機的其原因之一。
說到緊張感,《谍影重重》系列是一個代表,即使拍人物特寫鏡頭也是晃動的,或許許多攝影師都會藉助此種形式呈現出緊張感,但《峰爆》並沒有使用這種的形式。
《峰爆》是一部高要求、高規格的大災難大片,足以媲美荷里活A級製作。荷里活對A級製作的圖像輕工業產品品質是有國際標準的,都會有多樣的細節呈現出、有立體感,有足夠多高的表演藝術產品品質。但國內部份年長編劇討厭用大光圈實現焦外的感覺,在大熒幕上長時間看大光圈、淺景深會很不舒服,藉助大光圈固然能節省置景效率,但同時也會犧牲觀感,從這種角度而言這更像是文藝片的圖像。《峰爆》向荷里活A級製作看齊,力求觀眾們擁有沉浸式的觀感體驗。
趙曉時:拍《夺冠》時,80二十世紀的部份我和陳可辛編劇探討過要千萬別用膠捲拍,當時也做了許多試驗,膠捲和數字介質相同,圖像個性有非常大差異。
另一方面我們在四川地下溶洞實地考察攝製地,實景可以節約搭景的時間和成本,但是攝製條件惡劣,從專業的角度而言不具備可操作性,不過為的是效果我們最終還是選擇實拍。所以我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看景過程中我拉傷了腰,走山路、下巖洞都很困難,可是沒有辦法,身為攝影指導,關鍵的場景我無法缺席,只能咬牙堅持,進到洞裡去敲定每一個攝製細節,看閉路電視的這時候則趴著和大家溝通交流。時間緊、任務重、器材運送困難,選擇AB組配置會更有效率,三組可以在ABC洞之間依序替換,這種滾動作業就不能耽擱攝製。
另一個例子,一直以來都著重內容的李安編劇,為什么去和技術較勁,拍4K 120幀?他給出的提問是“即使我看見了,我就沒有辦法再漠視。”電視節目從標清、高畫質再到4K,解析度不斷升級,立刻8K電視節目就要步入生活,影片不必須在2K解析度駐足不前,自然要與時俱進。更何況,膠捲走過了100年,已經到達牆壁,但是數字攝影未來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也能呈現出更多細節、讓觀眾們更有沉浸感。
拍《夺冠》時用了48幀,但此次又拍回24幀,其原因是什么?高幀率嗎對攝製和整個中後期程序都會造成負面影響?
趙曉時:兩個主流攝像機國際品牌,到了專業層次的產品在機能和操控性上都足以滿足攝製要求,同時又各有特色。至於選擇哪一款,有一部分其原因是編劇個人喜好,比如說他就討厭某一國際品牌的美感信息系統,覺得接近他經典作品的美學表達;除此之外一個選擇國際標準,要依照相同影片類型選擇最合適的攝像機,所以,也不乏攝影師個人喜好問題。
而且《峰爆》假如用高幀率攝製如果,嗎意味著中後期工作量會變小,尤其是特技效率也會大幅度減少?
朱一龍在塌方裂紋裡攀爬,包含前面兄弟二人二人徒手滑雪,那些攝影機是怎樣順利完成的?
好口碑和高影片票房的背後,是幕後值班人員的艱辛付出。災難片在國產片中並不多見,全劇少於1300個視效攝影機的《峰爆》面臨眾多挑戰,不但對攝影、藝術等職能部門提出更高要求,在各方資源間找出均衡,實現影片最佳效果也是關鍵研究課題。
那一共用了多少臺攝像機?
但為什么最終沒有用那個方案?攝製女籃賽事會造成大量素材,採用膠捲的話,除了膠捲耗用和擦拭,後續剪接環節也會面臨困難選擇。是直接剪膠捲還是轉數字後再剪接?膠捲剪接費時長,假如轉數字,膠捲掃描成本是天文數字,多方取捨,最終還是選擇用數字攝像機。
趙曉時:我們此次用了ARRI ALEXA LF和ARRI ALEXA Mini LF,攝影機用了ARRI的SP定焦攝影機。選擇的其原因首先LF有大畫幅,我用的是1:2的畫幅比;另一方面我想盡量的通過大畫幅攝製,能記錄更多的細節,因而這一次在景深方面,如果太陽光條件容許,我最大光圈不能少於5.6,這種做的結果是讓觀眾們能在大熒幕上看見更多細節。
但常常溝通交流到最後,用言語已經很難精確敘述,此時我會建議拍點實驗片,《梅兰芳》就是這種操作的,當時籌備期較為長,很多場景先搭好了,就拍了一段給編劇證實。
趙曉時:我們始終堅持呈現出自然太陽光的創作經營理念,當然也有特例。兄弟二人兩人在水潭旁邊的場景,這個地方太空曠了,足足有40多米高,縱深也大,小洪用手電筒照高處的這個攝影機,我不敢他什么都看不見,也須要將大空間呈現出給觀眾們,而且就給高處打了一點光,但觀眾們在大熒幕上不能覺得突兀,也不能喪失空間感。
趙曉時:對的,你說的那個問題《夺冠》時就碰到了。《夺冠》也有許多中後期合成部份,比如說觀眾席等,但是當時的攝製也很緊張。但《夺冠》的中後期特技量較為小,《峰爆》全劇2000數個攝影機,和視效相關的攝影機1300數個,佔了一多半,假如用48幀拍,工作量減少太多了,而且中後期沒有做高幀率的選擇。
趙曉時:這兩部份真要去爬山操作難度太大,我們一比一還原塌方內部結構,人工搭建了一段草叢,觀感和真正的林間草叢別無二致;滑雪部份我們找了幾塊真正的石壁,中後期全景通過特技製備,配合下雪、救人帶給觀眾們身臨其境的觀感。
虛擬的攝製介入會不能對攝影有更高要求?
影片開場高架橋爆破、透水的場面很震撼,是在真實的高架橋裡攝製的嗎?
比如說《梅兰芳》要具有經典個性,影片聚焦傳奇故事情節和傳奇人物,攝影就要莊嚴許多;《一点就到家》講訴的是青年人創業的過程,和編劇溝通交流時,他希望呈現出一種開朗、風尚,合乎青年人的語境和調性,因而就使用了攝影機來回搖的形式,減少影片的娛樂性和喜感。
此次攝製用了什么攝像機和攝影機,選擇的其原因是什么?
เว็บไซต์นี้เป็นเว็บไซต์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พยนตร์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เกี่ยวกับโปสเตอร์ภาพยนตร์ ตัวอย่าง 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 ข่าวสาร บทวิจารณ์ เร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ภาพยนตร์ล่าสุดและดีที่สุดและบทวิจารณ์ภาพยนตร์ออนไลน์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ธุรกิจหรือ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โปรดส่งอีเมลถึงเรา (ลิขสิทธิ์ © 2017 - 2020 920MI)。EMAIL